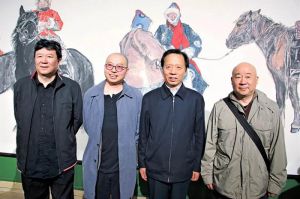意与古会 千秋如对
王赫赫兄是我所认识的诸友中最具古风意味的人物。当然,这也许源于我的双重想象,一是我理想中的古人,一是现实中的赫赫兄,然而,我却分明在“意与古会”中感受到两者性灵之间的静晤默对。
今人大多“谈古色变”,一则出于对“古”的崇拜与敬仰,以为不可企及,故退而远之;二则认为“古”乃过去之凝固僵化,呈现为永恒的停滞,故嗤之以鼻。“古”该当何解?又与当下是何种关系?我们可将“古”视为一种对于时间的感知和历史的意识,但如果历史仅仅是时间单线的前后推移,则“古”大概只能成为封存的过去;如果我们仅是着眼于当下与不可知的未来而一往无前,则“古”所能唤起的历史记忆与其表面的陈旧自然毫无价值。然而,在我看来,中国人的“古”与时间关涉不大,它更多的是关乎生动鲜活的生命存在与价值,外化的历史感恰是超越时空的生命意识的贯穿。古今之间可以通过生命性灵的对话获得融浑圆满,正如黄宾虹引西谚“太阳底下无新事”(There are no new thing under the sun),正如金城所言:“无旧非新,新由是旧,化其旧虽旧犹新,泥其新虽新亦旧”,如若简单的以新旧来判别古今,实是去古甚远,而若意与古会,方能千秋如对。
“意”如何“会”?庄子曰:“书不尽言,言不尽意”,意会只在一刹那间的若有所悟,如佛主拈花,迦叶一笑,只在以心传心。古人还云,“言不尽意,立象以尽意”,赫赫兄正是通过绘画这一媒介,将相隔千年的画家摄入“会”的一个刹那之间。在此,我却试图以言解意,只恐仅落于筌蹄而已。
唐代仕女“纤秾”、“绮丽”,而却能在形简笔实中凸显恢弘气象;两宋人物高韬飘逸,却是理法兼备,沉潜内敛;元季多隐士,淡墨轻岚中最见意味幽远;明清以来,虽整体式微,却有异军突起,怪诞奇古,以今世之情、超脱性灵达于千古之外……在我看来,中国人物画的历史进程都在赫赫兄的“意与古会”中瓣开、揉碎、重组,营造出可与今人相通的古雅趣味与超越境界。也许,我们可以将这些看起来形象相似、主题类同的小品书写看作是其鉴取古人的练习曲,但我却更愿意将其视为赫赫兄以“典故”意识接续文脉、直通性灵的自说自画。
“典故”多被视为典制和掌故,作为一种修辞手法,广泛用于诗文写作,俗称“用典”,借引用古籍中的故事或词句来丰富而含蓄地表达有关内容和思想。在绘画中,我想不妨以“视觉典故”称之。朱良志先生对此有着精辟分析,并以唐寅为例将其使用范围概括为“借图像呈现文献中的典故”和“绘画主题的典故接递”两种,还进一步总结道:“视觉艺术使用典故,不仅丰富了艺术的表达空间,而且由于典故是一种历时性的动态呈现形式,也会增加绘画独特的历史感”。赫赫兄的历史感在此不言自明,且不说于文献典故的续用却能转出己意,就其绘画主题而言,又可细分为二:一为文人雅事;二为道禅精神。前者如咏梅、觅句、听松、拜石、观莲、鉴古、看花、品茶等等,均是文人绘画系统中籍师自然之心反观自我的常见画题,画题的重演恰是赫赫兄与心仪的文人士夫之间的言说和交流,生命存在的主题在此得以延续。“我思老莲”最能见出个中真意,老莲之画常被誉为有太古之风、晋唐意味,其刻意追求的高古画境兹兹可见,然其意并非简单的复古或是往昔的眷念,而是在趣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性灵的还原与超越,从而肯定当下直接的生命体验。于此,“老莲思古”与“我思老莲”在六百年的时空间隔中幽然相会,思接千载,一刹那间碰撞出永恒的生命此在。
如果说,文人籍雅事自解尚耽于形迹,若有所隔,那么直追其后的道禅精神也许更能探触到生命觉解的真意。赫赫兄喜绘罗汉与高僧,或坐或憩、或行或渡,不拘于故事之传奇、情节之乖戾,而是强调以高古神情传达参禅悟道的瞬间会意,以澄明之境照见万物之精神,尤其是数张禅师造像,以相应佛偈自醒,借公案妙语显出机锋,所谓“穷神变,测幽微”是也。
言不逮意,如此解说怎能会得赫赫兄真意?但言已及此,又怎能不就其画中形式风格的“典故错综”续说一二,再则,今古画家之间的性灵对话不可能是面对面的言传意会,也非凭借文字,而需通过绘画“立象”得来,由此方可见出画家本色。在其画中,人物造像似从亘古而来,情态苍古端凝,笔致紧劲连绵,为唐代以来的高古一路;有意思的是,唐人垂柳、宋人古松、元人修竹、老莲桐荫、八大怪石、陆氏烟云(陆俨少)等配景在其笔下进行了大胆的交错处理,不仅在画面中配置得合情合理,如风行水上、云涌山头般自然无间,而且让这些大家熟识的形式风格相互激发,重获超越时空的生命,如南泉山庵主置于八大荒寒之山水、渡江罗汉行于陆氏变幻之云山等等,真耶幻耶?大有斗转星移、人是物非之感。其实,性灵之间的对话不在于一山一水、一树一石,也不在于某朝时风、某家路数,赫赫兄在营造这般引人入胜的自然虚景的同时,以一种超越历史表相的历史感确证了无论古今的生命恒在。
“用典”的目的并非回复过去,而是直指当下。“奈近来人心不古,都尚奢华”,《镜花缘》如是说;“人心不古今非昨,大雅所以久不作”,唐寅《恬古歌》又作如是观。当传统中国画一味按照西方文化的“时间进化”理论求新求变求异,当“古今之争“让中国画丧失生命之本真而舍本求末之际,赫赫兄倡言“意与古会”,并身体力行、潜心悟对,以“典故错综”的方式将古今之隔化为惬意的心领神会,便无疑具有了一种当下的价值:重寻生命的安顿。
古也好,今也罢,古今同心的生命存在才是真正的大雅之曲,若循此道,即为孤寂又若何?此中漫索,唯有意会。
中国美术馆 邓 锋
甲午初秋草就于望京
- 01 草原情味——观王赫赫中国美术馆展
- 02 “血战古人”——薛永年评论王赫赫
- 03 古韵今风——丁杰评论王赫赫
- 04 王赫赫:心驰太古 道在日新
- 05 《融古化今 ·正道弘毅》——王赫赫“弘毅”作品展访谈/田黎明
- 06 形式可以与内容分裂吗?——读王赫赫的绘画有感 彭锋
- 07 邱振中
- 08 梅墨生
- 09 刘万鸣
- 10 方向
- 11 刘墨
- 12 徐书城
- 13 吴为山
- 14 丘挺
- 15 梅墨生
- 16 李洋
- 17 王西京
- 18 拙朴清新说赫赫 文/范扬
- 19 见心明性,古为我用--谈王赫赫的书法 文/陈忠康
- 20 读《冯有兰自述》随感 文/王赫赫
- 21 赫赫其人其画 文\田黎明
- 22 如是我闻——赫赫和他的思想“图经” 蜕言
- 23 形式可以与内容分裂吗?——读王赫赫的绘画有感 文/彭锋
- 24 答振飞兄十问 2017.3.7
- 25 静观--谈赫赫的文心与绘画 文/田黎明
- 26 我与罗汉画 文/王赫赫
- 27 山水与禅悦 文\薛永年
- 28 学习班感想
- 29 "血战古人"——薛永年评论王赫赫 文/薛永年
- 30 意与古会 千秋如对
- 31 远行者需孤履 文/汪为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