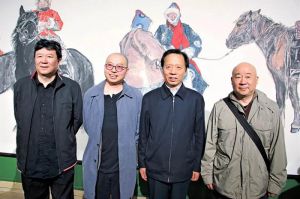我与罗汉画 文/王赫赫
曾有朋友问我:你为什么画罗汉?我一时竟回答不出。我确实没有追究过这个问题。后来想想,提问的朋友并不是画画的,而是搞史论的。问题的提出是他们的惯性思维。画画的哪里会管这些。总不会因为你今天画了个竹子,明天画了个马驹,而追问为什么要画这些。但经那位搞史论的朋友这么一问,倒让我认真的反思自己是如何喜欢上画罗汉的。
我起初所谓画罗汉是拿这桩事当作研究传统画法的一个路径。徐悲鸿说古之垂绝者继之。我对这句话相当认同。传统中人物画的分类较细,而罗汉画作为一科,单独地占有一席之地,且留存下来的亦复不多。所以那时我想努力深研传统,追“古法”,求“古意”。手头正巧有一本台北故宫编印的《罗汉画》一书,就对照着勾描。从贯休、周季常到吴彬、丁云鹏都摸了一遍。并将自己喜爱的宋元人的山石树木作为补景配置其间。但探索实践中问题很多,比如:明人画的罗汉确已不那么庄严肃穆,而有了世俗的味道,补景也承不起李郭那样的树法,所以又学习文征明。总之那时对于能见到的罗汉画都找来参看,旁涉配景又学习了些古人的花竹树石。既是对传统做一番梳理,也是对美院中所学做一个矫枉。画了一批《竹石罗汉》,算是总结。那时亦步亦趋的学,认真是有的,但又总觉不满足,不能自由地运用,更谈不到发抒胸臆。况且善学柳下惠,哪吒拆骨还父拆肉还母之类这样的教诲又时时存想。自己头脑中古意、风格、图式、传统、创造...又常碰撞纠结,不能融通。有人也讥为泥古不化。恰巧那时看了个陆俨少的展览,陆俨少说学传统没有什么打不出来,出不来是说明还没有打进去。这使我又鼓起了勇气,此一阶段只想着研究传统,逼近古人,而索性不去考虑变化,到某一时日自然水到渠成,想不变都不可能。后来我深知“时代性”是个伪问题,而中国画的延续与超越实是于古人之传统的解构中创作出来。既有王国维所谓“古雅美”,又必然带有时代精神。
说了这些,还是不能回答我如何就画起罗汉画而不是别的。这其中的延津剑合恐怕要用因果业力去解释了。两千零五年我曾有机缘临摹过托名弘一的罗汉画与丰子恺的《护生画集》。但那时对宗教类的绘画还不能纯然的以宗教的视角去看它。如果说陈师曾在论及宋代的罗汉画时说其已将宗教的色彩淡化,而附以文人画的趣味是可勉强解答风格上的流变的话,那么我的学习罗汉画也正是这样的一种状态。但也并非没有丝毫的宗教色彩在。记得当时正喜欢陈少梅。他有一幅《无量寿佛》,我也临摹一过。观其题跋,是说此画乃陈少梅父亲逝世一个月左右而作,恰巧我父亲也刚巧故去月余。如此巧合,我想我画此类题材必定冥冥之中有感于天人、生死、轮回...又岂是绘画本身所能涵盖?我临的那幅画至今仍保存于箧内,可以算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幅罗汉画了。二零一二年,我的那本《王赫赫画罗汉集》于天津人美出版之际,也说要报宗教局审批。后从绘画上看认为就是文人画嘛,也就作罢。
随着罗汉画学习与创作的深入,自己看了不少名作以外,也读了一些罗汉与佛教方面的书籍。以我之鄙俗,未敢言皈依佛门。然敬佛礼佛,喜闻佛法,心存悲悯是有的。以恭敬心作画,尤其是罗汉画,当然也是不可或缺。后来许多人同我讲:你画的罗汉画有些像你自己。我听了一笑。自己有何福德能修来罗汉貌呢?
- 01 草原情味——观王赫赫中国美术馆展
- 02 “血战古人”——薛永年评论王赫赫
- 03 古韵今风——丁杰评论王赫赫
- 04 王赫赫:心驰太古 道在日新
- 05 《融古化今 ·正道弘毅》——王赫赫“弘毅”作品展访谈/田黎明
- 06 形式可以与内容分裂吗?——读王赫赫的绘画有感 彭锋
- 07 邱振中
- 08 梅墨生
- 09 刘万鸣
- 10 方向
- 11 刘墨
- 12 徐书城
- 13 吴为山
- 14 丘挺
- 15 梅墨生
- 16 李洋
- 17 王西京
- 18 拙朴清新说赫赫 文/范扬
- 19 见心明性,古为我用--谈王赫赫的书法 文/陈忠康
- 20 读《冯有兰自述》随感 文/王赫赫
- 21 赫赫其人其画 文\田黎明
- 22 如是我闻——赫赫和他的思想“图经” 蜕言
- 23 形式可以与内容分裂吗?——读王赫赫的绘画有感 文/彭锋
- 24 答振飞兄十问 2017.3.7
- 25 静观--谈赫赫的文心与绘画 文/田黎明
- 26 我与罗汉画 文/王赫赫
- 27 山水与禅悦 文\薛永年
- 28 学习班感想
- 29 "血战古人"——薛永年评论王赫赫 文/薛永年
- 30 意与古会 千秋如对
- 31 远行者需孤履 文/汪为新